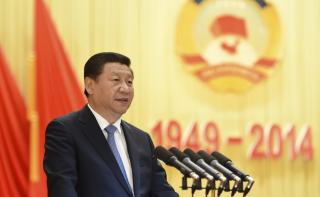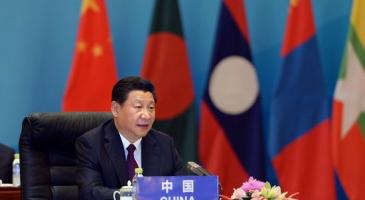在新疆地区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维稳的思路,终清一代基本保持下去,在促使新疆顺利纳入1800年之前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框架的同时,也保持了国家西陲比较持久的稳定,并最终在左宗棠西征、新疆建省之后,得以收获更多的改革红利。
平定回部献俘
古丝绸之路的主导权,终于再度回归中国之手。
1760年,中国大军彻底平息新疆地区(此前称为“回部”或“西域”,“新疆”之名称,按后来左宗棠的解释,即“故土新归”)的长期叛乱。在胜利捷报传向北京的同时,一个难题也摆到了执政者面前:如何建设新疆、发展新疆?
乾隆皇帝的行动是:复苏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繁荣。
简化行政审批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
此前,凡是前往新疆的商人,一律必须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乌里雅苏台城)“定边左副将军衙门”领取执照。乌里雅苏台远在漠北,内地商人们要先绕道这里办理手续,再万里迢迢前往新疆,如此一来,等于是筑起了一道行政壁垒,阻止商人入疆。
在战时,这一政策有其合理性,既便于政府控制入疆的商人数量,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不稳定,又便于政府调控入疆的商品种类,以优先满足军用。
平叛战争结束之后,乾隆的注意力放到了如何发展新疆经济上。而加大新疆的开放力度,鼓励新疆与内地的商贸,成为战略布局的关键。简化入疆经商的行政审批程序,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的第一个改革举动。
中央推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内地商人入疆,一律改由鄂尔多斯、阿拉善、推河、阿济等地的沿疆地方政府核发入疆执照。在圣旨中,乾隆明确指出:“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此次改革,“较之转向乌里雅苏台领照,程站可省四十余日,商贩自必云集,更于新疆有益。”
这样的改革,自然受到商旅的欢迎,这不仅是节省了40多天无谓的艰难跋涉,更提升了商人们对新疆-内地贸易的信心。
中央对于新疆的开放,不断加大力度,除了鼓励商人到天山北路经商外,还鼓励他们进入天山南路。乾隆皇帝多次亲自批示,阐述发展商业对新疆建设的关键作用,如“客民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耕亩日开,愚迁日众,则中外生计更饶”。乾隆皇帝还多次强调,在鼓励新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中,必须严格约束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谆谆教诲此事“须听商民自便”、“不可官为勒派”、“毋使青吏需索”。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一时之间,内地商民掀起了到新疆去的热潮,尽管新疆的条件十分艰苦,尽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一个宣示要安守本分的政府,似乎解除了资本的顾虑。
入疆的两条主要通道上,车旅不绝——一条经张家口、归化,走蒙古草原入疆,另一条是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前者是晋商、蒙古商人的主要通道,后者是陕甘及南方各省商人的通道。
中央还鼓励新疆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同样在1760年,乾隆在圣旨中提出:“回疆今就平定,所有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等部人,均为大皇帝臣仆,尔部如欲遣头目入期,以展归化之诚,必代奏闻。”而对于内地商人和外邦商人,清政府在新疆都给予低税优惠,甚至免税待遇,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1762年,乾隆再度发布上谕,对于“自平定回部以来”该地区的局势稳定、治安良好、民族和谐予以高度肯定,继而提出应“晓谕商民,不时往返贸易”,同时,强调指出:“贸易一事,应听商民自便,未便官办勒派……若有愿往者,即办给照票,听其贸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贩自可流通矣。”
在政府的鼓励及有节制的管理下,新疆与内地的经贸交流大规模地推进。“中兴以来,西陲底定,拓地周二万里之广,内地商贾持币帛以来者,论蹄万计。天山以南、玉门以西,昔为游牧佳场者,今则为商埠重地矣。”(《新疆图志﹒赋税》)南疆地区的“南八城”,也迅速成为贸易中心,如叶尔羌,“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西域闻见录》)
法制推动繁荣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出于维稳“羁縻”的短期需要,更多的或许是基于一种大国自信的战略远见。
对于新疆的成就,连英国人都心生艳羡。大英帝国著名学者包罗杰,在其初版于1878年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回顾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盛赞道:
“他们(中国人)能够给予当地的最大的恩惠当然是维持秩序。公平地在许多诉讼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中国行政长官的第一条信条。在这个混乱的地区一旦能安定下来,贸易就复活了。大为衰落的当地工业又重新活跃起来;外国企业也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中国政权很快就使之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
“但中国人并不仅仅以维持良好秩序为满足……他们自己还作出榜样,使旁人感到应予效仿。富于进取性的甘肃、四川‘和台’商人不仅到达哈密和吐鲁番的市集,他们之中有许多还深入到喀什噶尔本部,并定居在那里。这些难能可贵的经商者填补了在这个地区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补足过的空白,因为他们带来了高度的事业精神和实践的智慧,还有他们特有的东西——资本。
“随着这些‘和台’商人之后,财富和繁荣都增进了。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成了一等城市,1800年这个地区的人口达到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高)的数目。”
包罗杰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在贸易上一切不同民族之间也有完全的平等”,内地来的商人,“必须准备与浩罕人、喀什噶尔人、阿富汗人进行机会平等的竞争,他的籍贯并不能为他取得免税的优惠,或给他什么优于外国商人或当地商人的便利。”因此,如此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当地社会与当地商人。
而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怎样使用税收,它的行政管理以怎样的为公精神把税收用在当地的公益事业上”,包罗杰认为甚至都值得英国人学习。正是有着如此“为公精神”的政府,推进了新疆的普遍繁荣。
这是西方文献中罕有的对中国政府行政成果的称颂。包罗杰所总结的新疆成功之道,概括起来就是:
一、公平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公正,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二、廉洁高效的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三、敬业的商人带来资本、经验与市场;
四、平等的民族政策减少了无谓的冲突——此前及此后的历史都证明了,有任何偏向性的民族政策,对各方、包括受其庇护的一方都未必有利。
稳定地开放了5年之后(1765),新疆乌什地区发生暴动。暴动平息之后,对于内地商人入疆,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管理——“商民则北路携眷,而南路不得挚眷”,前往南疆的商人,禁止携带家属。后世一些人将此解读成隔离政策,实在有点刁难古人,毕竟,南疆限制的仅仅是商人不得携带家眷——在一个反暴恐成本高企的特殊时候,这样的限制符合情理。更重要的,这一限制令在半个世纪后也取消了。而即便在限制令推行的半个世纪中,除了曾对作为敌国的浩罕国商人实行过禁止之外,内地商人及外邦商人依然可以在新疆自由地经商。
当代美国汉学家濮德培认为,在当时的新疆,不同民族的“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得以获益”,而另一汉学家穆素洁也认为,乾隆时期新疆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发展,将该地区“引入国际贸易范围”。
南疆货币特区
这无疑是最为与时俱进的“铸剑为犁”,兆惠实际上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体现其对新疆维稳大局的自信。
以军功而铭刻史册的兆惠将军,在写给中央关于新疆善后的报告中,却不惜笔墨,详尽地论述了货币制度在稳定新疆和发展新疆中的巨大作用,提出要实行货币体制改革,发行自主货币。
此时新疆,面对的最大金融困境是白银外流。乾隆在1760年的一份上谕中,坦承新疆遭遇的白银外流:“内地所用银两,携至外藩交易,有发无收,将来恐致耗散。”
新疆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结构单一,不少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必需依靠与周边邦国的贸易,造成出超;二是南疆长期被准噶尔势力盘踞,包括货币在内的主权实际上难以行使。
在兆惠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议:“回部钱文应行改铸”。所谓“回部钱文”,是指此前在南疆地区通行的准噶尔货币。这是一种铜质铸钱,当地称为“普尔钱”。
当时世界上最为通行硬币,铸造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西方通行的所谓希腊罗马式,以打压法铸造;二是东亚地区通行的所谓中国式,以浇铸法铸造。新疆虽然早在汉唐就纳入了版图,但总是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动,而常常游离于主流之外。
兆惠率军收复南疆,重新铸币发行,即便在主权宣示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回部钱文应行改铸”,不仅是经济战略需要,也是政治战略需要。
兆惠提出的铸币方案有两种。
第一种方案是“照内地制钱,每一文重一钱二分”。“制钱”,即制式铜钱,外圆内方,对于铸造方式、含量、铭文,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一方案的好处,一是简单,直接将内地铸钱所用的模型带到新疆即可;二是便捷,可迅速将新疆经济融入全国一盘棋中。而其不利之处,一是不符合南疆当地人的使用习惯,二是新疆经济百废待举,一步到位与内地货币并轨,可能会给新疆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
第二种方案,是“即照回钱体质,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叶尔羌清文及回字”,即对南疆原先通行的“普尔钱”进行改造,铭文去除宗教教条,突出“乾隆通宝”这一主权标识,并使用汉满回三种文字。显然,这种折衷方式,既顾及了主权宣示,又顾及了当地的使用习惯。
乾隆其实并未在这两种方案中选择,而是做出了 “一疆两制”的第三种决策:在北疆地区发行内地的制钱,而在南疆地区,则采用兆惠的第二种方案,发行“新普尔钱”。
整个新疆地区,政府体制有三种形式,一是北疆地区的郡县制,与内地完全相同;二是吐鲁番、哈密及厄鲁特、哈萨克等地的札萨克制;三是南疆地区的伯克制。实行郡县制的北疆及实行札萨克制的吐鲁番等地,长期与内地经贸来往频繁,早已纳入了制钱的实际使用范围,可以一步到位推行内地的货币。乾隆的方案,是因地制宜的现实做法。
战争刚刚结束,铸造新钱所需要的铜材,短期之内还难以运抵新疆、尤其南疆,因此,兆惠建议:“现有铸炮铜七千余斤,请先铸五十余万文,换回旧钱另铸。”将铸造大炮的铜材,改为铸造钱币之用,这无疑是最为与时俱进的“铸剑为犁”。兆惠实际上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体现其对新疆维稳大局的自信。
“新普尔钱”弃用了此前“形椭首镜、中无方孔”的形状,而改用外圆内方,定重二钱,按照1:2的兑换率回收旧钱,次年改为1:1回收。如此优惠政策,大大加快了旧钱的回收速度。
与内地制钱多用黄铜、且“铅四铜六”的比例不同,“新普尔钱”“悉提净红铜而成,并未配铸他项铜铅”,铜的含量高达90%,色泽呈现红色,因此民间又称“红钱”。
“新普尔钱”开始发行后,南疆地区出现了铸币厂,最早是在叶尔羌,而后扩展到阿克苏、沙雅等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原先相当原始的铜矿业,开始兴旺。政府鼓励南疆民众开采铜矿,铜矿的规模得以迅速扩大、技术得以迅速提高,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新普尔钱”在整个南疆地区发行,大大超过了此前准噶尔统治下只有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三地使用铸币的局限,解决了南疆其它地区的货币“短板”,令南疆商贸流通提速。南疆各级政府设立集市;中央财政则对南疆棉布等,实行政府采购,输往北疆以换取马匹。这种“绢马贸易”,既盘活了南疆与北疆的资源,又提高了南疆与北疆的生活水平,南疆以“新普尔钱”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也得以不断壮大,为数十年后在全疆地区推行“新普尔钱”打下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南疆实行单独的货币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当地新生的经济。晚清时期,内地多次发生“钱荒”,导致银价暴涨、铜钱贬值,而南疆地区的“新普尔钱”则因保护而一枝独秀,令南疆避免遭受内地货币波动的池鱼之殃。
对于政府来讲,南疆实际上已经成为货币特区,大大减缓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原先需完全从内地调拨的军饷和新疆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有相当部分可以“新普尔钱”替代。
压服西边强邻
防范阿富汗及后来崛起的浩罕国,就成为清帝国中亚政策的准则之一。在乾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通商贸易与军事震慑两手齐备,两手都很硬。
乾隆皇帝的丝路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是西边的强邻阿富汗,时称“爱乌罕”。
按西方史学界的说法,彼时的“爱乌罕”,是一个与中华帝国、“准噶尔帝国”(实为中国之叛乱势力)在中亚地区足以鼎立的一方,领土面积包括了今日的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以及印度旁遮普地区,其地位及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30年后派遣马戛尔尼到访的大英帝国。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为“阿富汗帝国”,或者杜兰尼帝国。
阿富汗帝国皇帝爱哈默特沙(Ahmad Shah Durrani,此处循《清史稿》译法),也是一代枭雄。当中国在新疆的平叛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阿富汗帝国耗费数年时间,积极筹建反华同盟,于1757年计划挥师东进,与中国争夺南疆。这场可能的战争,对于已经在新疆陆续征战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平叛部队来说,压力不小:毕竟供给线过于漫长,且已经是疲敝之师,要与以逸待劳的敌军对抗,风险不小。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阿富汗帝国后院起火。这一年年初,被其征服的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发生了暴动,当地军民起而反抗阿富汗占领军,逼迫爱哈默特沙放弃东进,回师印度,镇压德里的暴动。这给了中国一个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顺利地结束了平息南疆暴乱的战争。
阿富汗帝国稳定了印度后,却再也无力东进,因为此时,被后来的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影响到亚洲了——英国人来了。就在同一年(1757),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一举击败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孟加拉王公,取得了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为最后征服印度奠定了基础。无论是衰弱的莫卧儿帝国、彪悍的阿富汗帝国、还是强大的中华帝国,都将不得不面对这个从未遭遇过的劲敌。
在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中国与阿富汗都无心再发动新的战争,中国收复南疆之后的第三年(1763),阿富汗帝国选择了向中国称臣纳贡。
阿富汗帝国遣使上贡,当然是乾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成果,因此他十分重视,为接待事宜就曾一天内连发三道圣旨。第一道圣旨要求使节团所经过的“沿途各督抚,豫备筵宴”,热情接待,“爱乌罕系一大部落,其使人初次经行内地,天朝百技,俱所未睹,所有经过各省会,理宜豫备筵宴,陈设戏具,以示富丽严肃。”第二道圣旨说,对于阿富汗的使节,“理宜派出大臣护送。”第三道则是给阿富汗使团回程时,提供免费的骆驼,驮运“赏赉物件”,考虑得极为周详。1763年的正月初六(2月18日),乾隆在紫光阁宴请蒙古、回部外藩时,阿富汗使节是重要客人。三天后(正月初九),乾隆在畅春园之西厂进行大阅兵,阿富汗使节仍然是座上贵宾,接待规格很高。
然而,半个月后(正月二十四日,1763年3月8日),乾隆却在发给军机大臣的圣谕中说:“爱乌罕爱哈默特沙,初次遣使入觐,曾降旨各省督抚,沿途筵宴。今该使臣礼毕,回伊游牧地方经过处,应供给之项仍当妥协照料,不必筵宴。”取消了此前沿途接待宴请的待遇。
原来,在那些表面上洋溢着温情的觐见背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阿富汗使节居然拒绝叩头!这场争论,没有被记载到堂皇的正史中,但在正月初四(1763年2月16日)乾隆写给新柱等人的满文信中,有清晰的记载:“今爱乌罕使臣抵达后,虽跪呈奏章,却不肯叩头,恳请仍以伊等之礼朝觐。军机大臣等责称,尔汗遣汝何为,莫非不是前来朝觐?大皇帝乃天下一统之君,不但尔爱乌罕,凡俄罗斯、西洋人以及从前准噶尔人等来朝,无不行以叩拜之礼。君即如天,尔等难道亦不拜天乎?等语。反复晓示,和卓方转行叩拜之礼,但终究勉强。”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
这一“叩头”事件,比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的“叩头之争”,足足早了30年。但是,在这背后,并非乾隆真的为了所谓的天朝脸面,而是有着更为重大的战略考量。
乾隆皇帝在写给叶尔羌官员的满文信件中,指出:“纵览爱乌罕所遣使臣等举止,便知爱哈默特沙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久而久之,恐巴达克山人等或与安集延等处之人,伺机纠集骚扰我回疆地方,俱未可定。”因此,乾隆要求驻守在西域的军政要员们,“暂缓办理哈萨克事宜,要以全力应付回疆地方,一旦用兵,即遵陆续所降谕旨而行。”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
接见阿富汗使节,是乾隆本人的一次摸底调查。对于阿富汗帝国的好战与野心,乾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其遣使朝贡的虚荣中,而是清醒地做出了两手准备。
1763年2月23日,乾隆向阿富汗使节颁发了赐给爱哈默特沙的敕书。这是一份表面十分客气、其实却是绵里藏针的外交文件。
乾隆先对爱哈默特沙“远在外藩,向慕仁化,遣使入觐”的“诚悃”表示赞赏,并给予丰厚赏赐。而后列举了爱哈默特沙的若干征伐,指出:“尔又云欲往攻布哈尔,闻已归附中国不便侵伐,足昭恭顺之忱。”乾隆说:“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且如尔奏、数年来各处攻战,未获稍安,则尔之属人,亦殊劳苦,尚其和协邻封,休养部落,俾群享太平之福,以受朕恩泽于无穷。”
从文字上看,乾隆是劝导爱哈默特沙少折腾、不打仗,但“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一句,却含有浓烈的警告成分。叩头的礼仪事件之后,防范阿富汗及后来崛起的浩罕国,就成为清帝国中亚政策的准则之一。在乾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通商贸易与军事震慑两手齐备,两手都很硬。
低税未必有效
最初出于“羁縻”的税收优惠顶层设计,终于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丧权辱国。而这,比鸦片战争足足早了7年!
南疆初定,乾隆大力实行商贸开放政策,税收优惠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最初的税制,沿用了准噶尔的旧税率,即本地商人10%,外来客商5%。但不久,为了鼓励商业,这个税率又下降了不少,对于交易量很大的牲口贸易,本地商人为5%,而外来客商为3.33%(三十分之一),“其余皮张缎布,仍照旧例收纳”。
这一相当优惠的税率,自1759年开始成为大清国在新疆南部地区的法定税率,甚至,《户部则例》中还规定,对于来自巴尔替尔、克什米尔前来进行牲口交易的客商,税率低至2.5%(四十分之一)。而对于途经南疆的外国贡使团的随贡贸易,再给予半税、甚至免税的优待。
税收优惠力度如此之大,极大地促进了南疆地区的商业贸易,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向中央不无得意地报告:“现在回部安静,其布鲁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贸易之人,络绎不绝。”
如此低税,当然是为了“放水养鱼”,外资大量进入新疆。而在经济上的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相当重要:以低税换取政治上的安宁,“使各外夷凛遵天朝法度”。怀柔施恩是关键,经济利益其实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不幸的是,这种着眼于“羁縻”的顶层设计,到了基层执行者的手中,“柔”性被过度放大,尤其是一味减免外商税收,日渐成为常态,外商实际上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本应恩威并施的以外贸为工具的外交,“恩”成了唯一工具,“威”则荡然无存,反而示弱于外。
与南疆进行贸易的诸多汗国、土邦、部落中,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哈萨克、布哈拉及浩罕,而尤以作为地区强权的浩罕国为主。浩罕国虽从1759年开始对清政府表面称臣纳贡,但实际上对南疆怀有极大的领土野心。浩罕商人遍布南疆各地,成为低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但其对此不仅丝毫不领情,反而四处宣扬这是因为中国出于对浩罕国的畏惧。
凭借其作为地区强权的国力依托,及在南疆境内的巨大经营网络,浩罕商人不仅承包其它外商的进出口,申请免税,从中渔利,甚至有组织地进行茶叶和大黄的走私,根本无视中国法律。更为过分的是,浩罕国甚至向中国提出,将自己的税收机构派驻到中国境内,对在华经营的浩罕商人征税。此举的真正目的,是要替换中国政府所认可的 “呼岱达”——在华浩罕商人自治机构的领袖,将在华商人的自治机构改造为浩罕政府的外派机构,直接将其行政权伸展到中国的境内。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尔霍罕(浩罕)部落,不过边外小夷,天朝准令来往贸易,己属格外施恩,今尔敢为无厌之请!”清政府还希望浩罕国能换位思考:“天朝之人,岂无在尔处贸易者”,如果中国因此也要求“在尔境内添设官员,稽察税务”,无疑是 “越界之事”,这是中国政府“不肯为”的。
苦口婆心的说理,毫无作用。当大小和卓在南疆发动多次叛乱,浩罕国不仅为其提供庇护,活跃在南疆的浩罕商人甚至还给予积极配合,这导致了清政府对浩罕实施贸易禁运,浩罕则悍然出兵侵入中国。
吊诡的是,双方最终在1833年达成议和,清政府居然同意了浩罕在中国境内的南疆征税的要求,其对象不仅限于浩罕商人,甚至包括别国商人。最初出于“羁縻”的税收优惠顶层设计,终于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丧权辱国。而这,比鸦片战争足足早了7年!
《剑桥晚清史》曾列举了十八世纪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除了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欧洲人的到来”之外,还有两个就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及“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后两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第一个变化。“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是‘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
新疆地区的开拓、乾隆版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行,正是这种“质变”的关键一步。
即便有诸多瑕疵,在新疆地区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维稳的思路,终清一代基本保持下去,在促使新疆顺利纳入1800年之前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框架的同时,也保持了国家西陲比较持久的稳定,并最终在左宗棠西征、新疆建省之后,得以收获更多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