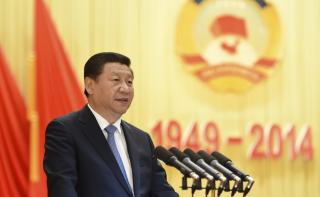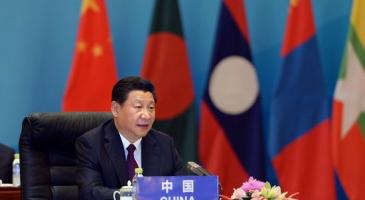如果没有学界对“一带一路”冷静严肃的科学研究,完全依靠政府部门的倡导和舆论的鼓噪,很容易将“一带一路”滑入“大跃进”的泥淖之中。
“一带一路”是由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并由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等部委规划设计的重大倡议,并非是源自学术界长期研究的产物。因此,在“一带一路”研究上,已经呈现出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问题,迄今为止,学界对“一带一路”的贡献还很不够,除了更多媒体学者和公共意见领袖在喋喋不休与笔耕不辍外,大多数严肃学者特别是最一流的学者对“一带一路”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还不是一门严肃的学问,随着“一带一路”热在中华大地的迅速兴起,整个社会处于“以吏为师”的状态。
显然,此种状况不能持续太久,否则,后果会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没有学界对“一带一路”冷静严肃的科学研究,完全依靠政府部门的倡导和舆论的鼓噪,很容易将“一带一路”滑入“大跃进”的泥淖之中。尽管“一带一路”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重大倡议,但最终还要专家学者来科学论证,部委会签在根本上不过是政策沟通和利益协调,意见领袖和媒体舆论也仅仅是发挥解放思想和社会动员的作用,“一带一路”能否真正走得通,还要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介入。说到底,“一带一路”要走得远,必须成为一门学问才能真正获得沿线国家的认可、接受和尊重。
那么,“一带一路”学应该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如果检索一下当下各学科对“一带一路”的初步参与来看,“一带一路”并非某一独立学科所能涵盖,一切文、理、工、医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都在“一带一路”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地位,从“一带一路”关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早期规划来看,可能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在建筑、土木、水利水电、机械工程、环境工程、通信技术等理工科专业可能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当然,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园区、贸易、金融和民间交流等议题,也需要经济、管理、社会、政治、人文、历史、法律、传播、心理等众多人文社会学科的大量介入。因此,“一带一路”学可能推动中国学科沿着三个方向向前发展:
一是文理工医多学科交叉化趋势。
自18世纪以来,随着学术工业化趋势的发展,大学内部的学科发展日益细化,按照学科分级分裂为越来越多的院、系、所、中心,乃至于更为微小的研究室、实验室和研究项目。此种学术分工的好处在于能够集中精力锁定某一微观问题进行“显微镜”下的精确研究,缺点在于缺乏对学科整体的关注,对研究对象的全局性和整体性变动缺乏敏锐性,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迷雾,甚至陷入资源争夺、权力竞争的官僚病而不能自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加强通识教育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性,但受制于复杂的利益矛盾,协同难度极大。
“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协同参与,要求各个学科打破门户偏见,突破院系所“山头主义”的藩篱,共同参与到某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中来,依靠多学科群体攻关才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目前,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更多是从某一学科角度出发开展的分散研究,且集中在经济、国际关系与外交、历史、文化与文明等领域,缺乏综合性和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尤其是明显缺乏理工科出身的科学家对该问题的研判,这根本上是由当前学科分立的体制机制造成的。显然,如何推动大学和科研院所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学发展的瓶颈性问题,应该引起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将其纳入中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制度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作为一种过渡办法,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应尽快组建跨院系所的学科交叉平台,比如通过设立“一带一路”研究院,以新型智库的机制来推动多学科交叉,该智库可以作为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在人事、财务、科研评价等方面实行机动灵活的政策,为“一带一路”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目前,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的重阳金融研究院就是此种制度创新的典型案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对“一带一路”的诸多政策建言都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面。
二是产学研管多部门一体化趋势。
作为一项事业,“一带一路”需要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众多行为体协同合作才能稳步推进,而且需要他们在信息、知识、资源、人才等各个方面要实现共享和自由流动,这是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条件。然而,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度的影响,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条块分割的格局根深蒂固,存在着很多体制机制性的障碍,很难实现多部门一体化。
“一带一路”要求打破条条块块的限制,寻求在更大的范围内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决不是某一个部门垄断的“蛋糕”,是包括党群、财经、政法、文教、外事、宣传、国防等众多领域的共同事业。因此,建立“一带一路”学不能依靠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系统,要寻求在研发、实业、管理和教学等多个部门之间推动一体化,此种一体化不是全面的一体化,而是围绕某一共同议题在展开的议题性联盟(Coalition of issues),此种议题性联盟旨在解决“一带一路”中的某一瓶颈性问题,实现关键环节和关键领域中的群体攻关。比如在设施联通方面,围绕通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组织电信、移动、网络、媒体、传播、管理、通信工程等众多领域中的科学家形成若干攻关团队,对“一带一路”通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出科学的论证,并与沿线国家的同行协商一个可行的实施方案,最终上升为政策规划和操作日程,为推进“一带一路”通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疏通障碍,提供智力支持。
同时,要改变以往依靠课题竞争性申请的传统做法,通过建立科学高效的研发服务平台,推动多部门协同创新,并在制度上打破依托某一部门和单位的做法,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建设产学研管联动的网络型智库。此种网络型制度的典型案例就是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院长领导下,该研究院将中央各涉农部委的分管领导、各大学和各智库的农村问题专家以及一些重要的涉农企业负责人集中在一起,组建了一个跨部门、跨领域和跨学科的网络型智库,对中央农村工作提出了大量富有智慧的新建议,对我国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是国内国外多主体网络化趋势。
“一带一路”尽管是由中国提议,但建设“一带一路”并不仅仅是中国一家的事情,涉及到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根据“一带一路”的“开放合作”的原则精神,它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世界上任何愿意参与的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相应地,“一带一路”学也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人的努力,应该广结天下英才,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体的对话和交流,充分吸纳多元文化的智慧和创造力,共建“一带一路”学,要求中国和沿线国家乃至整个国际学界建立更大范围内的多主体参与的研究网络。
推动“一带一路”学网络化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是组建“一带一路”智库联盟,采取加盟联络的方式,将世界上致力于研究“一带一路”的研究机构、研究项目和研究人员整合在一起,为智库搭建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的交流平台,共同开展对“一带一路”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可行性强的政策研究。据粗略统计,仅中国国内就有60多家与“一带一路”直接相关的智库,在国际社会中就更多了,如果将这些志同道合的研究机构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网络型智库,并加强智库间的对话和交流,对于建设“一带一路”学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在中联部的牵头下,国内“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已经成立,而且发展势头很快,这是符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重要举措。
“一带一路”学不仅需要智库的深入研究,更需要培养一大批各行业急需的建设人才,这就需要在推进“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的同时,也要尽快推进“一带一路”大学联盟的建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众多优秀大学,每年为社会培养大量人才。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内,由于受西方国家领先世界发展水平的影响,大量最优秀的学生都奔赴欧美发达国家留学,在培养目标和培养重点上更多符合发达国家的需要,最优秀的学生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缺乏了解,这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对“一带一路”学的建设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要通过组建“一带一路”大学联盟,将沿线国家的大学资源整合在一起,建立类似于美国常青藤联盟那样的教师、学生和校友联系比较密切的大学联盟,为“一带一路”不断输送更多高素质的紧缺人才。当然,推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和大学联盟并不是追求规模效应,而是要创造资源共享、研发协调和人才资源优化的机会,通过联盟这个平台,实现彼此之间的互联互通,为资源优化配置和推进深层合作创造条件。
150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谈到美国民主的优点时强调了美国发达政治科学对美国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有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当下,作为一个新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事业能否最终成功,也将取决于是否建立发达的“一带一路学”。因此,在今后,要通过推进文理医工多学科交叉、产学研管多部门协同和国内国际多主体网络的建设,实现强有力的智力开发和智慧创造,为“一带一路”开山辟路,保驾护航,为推进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人文包容提供强大精神武器和理论武装。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