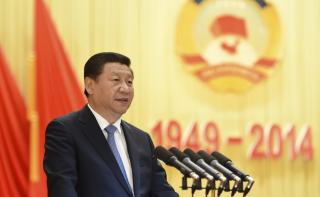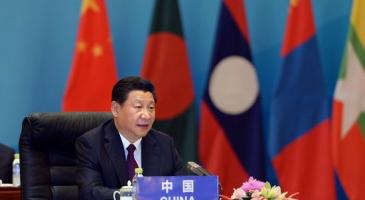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勾画出一幅看上去很美的蓝图。这一蓝图描绘了条条大道从欧亚大陆和印度洋地区通向中国的远景:“一带一路”战略基本涵盖了中国几条主要连接西南和西北邻国的路上通道(欧亚大陆),路海通道(中南亚),以及海上通道(环印度洋地区)。
这些经由不同方向、不同国家、不同环境的“路带”所涵盖的地域大部分是穆斯林国家或地区。所以从文化和宗教的视角看,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看作是中国对穆斯林世界的战略亦不为过,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走向。
但是,无论是地理或物理上的“一带一路”,抑或是文化和宗教意义上的“一带一路,” 都不是平坦的康庄大道,而是崎岖不平、错综复杂,充满了挑战。这一方面是由于“一带一路”沿岸或沿线国家的地理、政治、宗教、文化、制度、法律等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决定。而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新疆问题,即作为穆斯林国家的东南亚、中南亚和中东穆斯林国家对中国天山两麓或新疆问题的态度,甚至政策的看法。
在针对主要是穆斯林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开启之后,中国不计其数的各种有关“一带一路”的话语、叙事、研究、会议等都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憧憬着这一战略对亚洲乃至世界格局的改变和重塑,而却忽略了新疆地区问题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负面影响和现实挑战。由于历史(如奥斯曼帝国)、宗教教派(广义的逊尼派)甚至民族(如广大的突厥世界)的广泛关联,穆斯林世界在中国启动 “一带一路”战略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升对新疆问题的关注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疆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而且也日益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穆斯林国家的重大关切。笔者在与东南亚和中东穆斯林的接触和交流中深切体会到, “一带一路”沿线穆斯林国家对新疆问题的关切可以用两个“毫无例外”概括:一是所有穆斯林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支持中国在新疆的反恐;二是所有穆斯林国家(从官员到民众)都毫无例外地关注和忧虑新疆地方政府推行的赤裸裸反宗教政策,如强迫维吾尔退休公职人员(如教师)签订不得参与宗教活动的担保书、对妇女着装、男人蓄胡的粗暴干涉、禁止跨村礼拜、针对维吾尔人的哨卡/路卡以及地方政府强迫维吾尔商铺兜售烟酒等挑衅性地方性法规和实践。
穆斯林国家对中国国家层面的反恐支持和对新疆地区的反宗教实践的担忧,揭示了新疆问题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业已造成的负面影响。由于维吾尔问题的发酵和传播,和新疆直接接壤的路路通道和路海通道(北疆的欧亚大陆桥和南亚的喀什-瓜达尔路线)面临着直接的重大安全隐患。尽管中国国内鲜有报道,但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频频遇害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当中国平民遇害后,已有巴基斯坦塔利班公然宣称是报复中国的维吾尔政策。与喀什-瓜达尔路海一线相呼应的是,由于中国政府对缅甸军政府的长期支持,巴基斯坦塔利班内的罗兴亚智囊已经将罗兴亚穆斯林的灾难归罪于中国,并发誓要攻击中国目标。诸如此类的境外安全挑战同中国的新疆地方政策直接相关。
除了因为新疆地方政策而恶化的境外“一带一路”的安全环境之外,新疆现象或新疆化趋势也在向内地穆斯林聚居的省份传染。如2014年云南发生新疆籍暴恐份子袭击昆明火车站之后,云南地方政府(以及周边省份)不但清理当地的维吾尔人(直接阻止业已实践的镶嵌式多民族住居格局和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步伐),而且掀起所谓的“两清”运动,出台政策强制性遣返在云南求学的其他穆斯林民族(主要是回族)的老师和学生,居然将内地穆斯林延续几个世纪的游学传统作为打击目标。
这种“恐疆症”和地方性懒政造成的紧张,不但历史地勾忆起云南回族穆斯林在60年代和70年代分别遭遇的“四清运动”和 “沙甸惨案”所造成的痛苦回忆和巨大创伤,而且也现时地“新疆化”云南当地的民族宗教政策,直接危害“一带一路”战略在云南和东南亚穆斯林国家的实施。
无独有偶,近来在“一带一路”重镇西安闹得沸沸扬扬的陕师大禁头巾事件,便是直接由新疆籍的行政管理人员挑起,试图把他所熟悉的、已经造成新疆社会紧张、民族冲突的失败政策和经验移植到内陆。这不但破坏了内陆的民族文化和谐生态,而且也造成了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紧张和文化冲突。